国外博物馆,美术(狭义的美术,以绘画、雕塑为主)最受关注
2018-01-26 22:22:06 来源:中国艺术报|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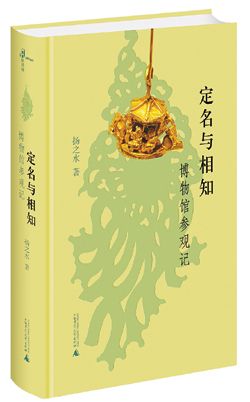
《定名与相知——博物馆参观记》 扬之水 著
我不喜欢赶潮流,但我走在参观博物馆潮流的前面
参观博物馆时下已成潮流,我从来不喜欢赶潮流,因此不妨坦率说明,我是走在这个潮流前面的。二十年前,我从遇安师问学,老师的授课很多时候就是在博物馆里。同时老师也告诉我做学问的方式,即准备某个专题之前,先要做长编。长编的内容包括文献,也包括图像,长编做得好,文章的成立就有了保证。当然那时候博物馆的情况不论展陈条件还是布展方式都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并且通常不允许拍照。那么就是一面阅读图录,一面到博物馆向实物求证我的阅读判断。这样做下来,大有收获,且体会到参观博物馆的种种好处。二十年来,从国内到境外,从东南亚到欧洲、北美,跑了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同时也逐渐把参观展览作为扩展见闻、搜集资料的治学方法。
国外博物馆,美术(狭义的美术,以绘画、雕塑为主)最受关注,参观者追求的是艺术的滋养。世界各大博物馆,如埃米尔塔什博物馆(冬宫) 、大英博物馆、卢浮宫、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均以“他者”之物为多(最近一期的《三联生活周刊》是大英博物馆专辑,题目就是《看懂大英博物馆:在一座建筑里思考整个世界》 ) 。国内大小博物馆正好相反,收藏品几乎全是“自家物” ,而鲜有“他者” ,这是特点也是缺失。随着中国考古走出中国,情况或许会有变化,但至少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哪家博物馆有意识留意收藏国外文物,当然现在这种收集工作已经很困难。国外文物展近年办了不少,有些还颇具规模,又有引进文物的轮展,此外,中外文物对比展也成为一个思路,比如世纪坛举办“秦汉与罗马” ,南京博物院举办“法老王:古埃及文明和中国汉代文明的故事”“帝国盛世:沙俄与大清的黄金时代” 。 《中国文物报》每期都有相当篇幅讨论博物馆的展览策划与设计,这也是去年创刊的《博物院》每期重点关注的问题。

金缕百事吉结子(浙江临安杨岭宋墓出土)
再回到本题,国内博物馆的藏品结构,使它成为参观者直观了解传统文化的一条途径,这里不说“捷径”而说“途径” ,即因为“直观”之后还需要理解和消化。博物馆是文物之聚英,也便于聚焦,但展品往往是脱离当日环境的,虽然展板多会提供若干背景资料,并且也有讲解员的解读,不过依然需要我们的深入思考,因此读“物”之后,仍需读书。青年作家张定浩的《爱欲与哀矜》中有一篇文章题作《 “你必须精通重的和善的” 》 ,这句话的后面是“以便也能这样地去和轻的作较量” 。这是引述小说中一位作曲家谈音乐的话,张定浩用它来说读书,我以为它也可以用来说读“物” 。比如关于一年一度的正仓院展。早先出国不便,往正仓院看展的中国人很少,因此关注正仓院藏品的多为学界中人,而又多是专门家,近年出国已成寻常事,专程赴奈良看展也很平常,关于正仓院特展的宣传便逐年增多,却不免褒扬过当,如称“这座位于奈良东大寺的宝库,保留了迄今为止种类最丰富、最全面、且最有价值的唐朝艺术品” 。“可以说,想要亲见唐朝最准确、最完整、最丰富的文物,正仓院是唯一的选择” 。说出这六个“最”以及随之而下的“唯一”之判断,后面应该有怎样的知识背景?对唐代文物有没有全局在胸?至少,是否看过“何家村”与“法门寺” ?是否看过几个唐代专题的展览?
据说央视近期播放的《如果国宝会说话》大受欢迎,这很可以理解。当代人活得太匆忙,因此每每满足于表面的知识,“短平快”的传播方式最受欢迎。然而不经过深入思考而生出自己的心得,表面的知识便会永远停留在表面。
“读图时代” ,开放的博物馆为我们打通“文”与“物”
虽然近年开展的“大众考古”为大家提供了了解考古实践的机会,但能够前往考古现场的“大众”实际上仍是“小众” 。博物馆则不然,它不像考古现场那样不得不有诸多限制,并且还提供了免费开放、允许拍照的条件,因此走进博物馆的真正是大众。“读图时代” ,这是我们特有的幸福。当然,“读图时代”对于学者来说,不是唯一的窗口,而只是增添了一条治学路径,增加了一种思考方式,使得看展览也成为一项治学方法,我把它称作“读物” 。
好比欣赏一首诗,吾人总是先要知道诗里的典故:故典、新典,典故用在这里的意思,然后是整首诗的意思。面对器物,也可以像读诗那样,看它的造型,纹样,设计构思的来源,找回它在当日生活中的名称,复原它在历史场景中的样态,在名与物的对应或不对应中抉发演变线索的关键。
沈从文从小说创作转向文物研究,虽然有着特殊的原因,但从文物与文学的关系来说,这种转变其实也很自然。近年大学建立了博物馆学,不知道学习科目是怎样的,我想象中,应该是围绕“博物”二字:工艺、科技、植物、动物,风土人情,而这些门类也都与文学有关。“文物”与“文学” ,两个词组都有一个“文”字,“文”本身即有多解,“文”与“物”组合,“文”与“学”组合,又有多解。我关注比较多的是“文心” ,小说诗歌戏曲的创作是“文心” ,“物”的设计制作同样也是“文心” ,本来二者是文心相通的,只是时过境迁,二者分离,因此必要想办法重新拼合。
近年博物馆的兴盛发达,博物馆人员构成的改变,博物馆的开放形式以及展陈方式的变化,都为我们提供了打通“文”与“物”的方便。这一从未有过的条件如果不去充分利用,就太可惜了。 《定名与相知》的副标题作“博物馆参观记” ,便意在强调所获新知的主要来源。参观博物馆,已经成为近年的一种生活方式。而在博物馆里我们老两口常常会与朋友相遇,可见采取这一生活方式的远不止我们一家。
常常在博物馆门前看到挂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牌子,爱国主义包括的内容应该很丰富,简单说是对自己传统文化的了解。在书本上看不到的知识,到博物馆去看——博物馆自然要有这样的担当,即利用直观的优势,为观众提供准确可靠的知识。

定名与相知,原是我为自己的研究所制定的目标
收入《定名与相知》的一组文章,都是近年国内外博物馆参观所见与所得。定名与相知,原是我为自己的研究所制定的目标,在这里也可以作为观展的总结。某物叫什么名字?什么用途?这是面对文物常会产生的一种最为直接的感受,是自我提问,也是我最常面对的来自朋友的提问。对自己而言,这是观展收获,另一方面,这部分内容也多为博物馆即时采用,因此由个人的心得而直接成为公共知识。这是很教人感觉欣慰的,为此付出的万千艰辛,算是得到了最高的回报。
《文心雕龙·史传》第一节说:“开辟草昧,岁纪绵邈,居今识古,其载籍乎。 ”刘勰的时代,欲接通古今,惟有文献一途。然而现代考古学的创立以及逐步走向成熟,却为我们走进古代世界揭示了更多的可能,也完全有条件使几乎被遗忘的名物学成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
今天的“名物研究” ,就研究对象而言,与“古”原是一脉相承,我把它定义为研究与典章制度风俗习惯有关的各种器物的名称和用途。它所面对的是文物:传世的,出土的。必要解决的是两项:第一是定名,第二是相知。定名,解决的是“物”的问题,即作为物,它的名称与用途。相知,解决的是“文”的问题,即它承载的文化信息究竟是什么。也就是说,定名,方可以使之复活;相知,方可以使之复原。
关于定名,我以为,对“物” ,亦即历史文化遗存的认识,便是从命名开始。当然所谓“定名”不是根据当代知识来命名,而是依据包括铭文等在内的各种古代文字材料和包括绘画、雕刻等在内的各种古代图像材料,来确定器物原有的名称。这个名称多半是当时的语言系统中一个稳定的最小单位,这里正包含着一个历史时段中的集体记忆。而由名称的产生与变化便可以触摸到日常生活史乃至社会生活史的若干发展脉络。
所谓“相知” ,即在定名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某器某物在当日的用途与功能,亦即名与物的还原。相知当然最难。借用哲学家的语言,可以说,我们必须学会“倾听” ,亦即在文与物的相互呈现中“倾听” 。我的理想是用名物研究建构一个新的叙事系统,此中包含着文学、历史、文物、考古等学科的打通,一面是在社会生活史的背景下对诗中“物”的推源溯流;一面是抉发“物”中折射出来的文心文事。希望用这种方法使自己能够在“诗”与“物”之间往来游走,在文学、艺术、历史、考古等领域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一个特殊的角度重温古典。对我来说,这样的考证过程永远有着求解的诱惑力,因此总是令人充满激情。
总之,定名与相知,这是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定名是针对“物”而言;相知,则须出入于“物”与“诗”之间,以此打通二者之联系。我把它作为研究的目标,也用它来检验自己的成绩,同时更希望读者也用这个标准来检验我的著述。至于这一工作的意义,我只能辗转引用老友李旻来信中所引述的一段他人对他人的评价:“西哲阿冈本(Agamben)说‘名物是思想诗意的瞬间’ ,大致如此吧。看见研究道教的吴真说,薛爱华的诸多研究,都令人信服地表明:表面上,名物似乎只关乎人类的日常生活,无足轻重,而实质上,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名物无声却又具体而微地说明着人类的生活方式,承载着诸多文化史、精神史与制度史的意义。 ”
张定浩曾为拙著撰写过两篇书评,在评述《中国古代金银首饰》的一篇里特别提到关于具体物事的形容,他说,“这样的白描文字,似易实难,因里面全然都是具体的名词和动词,又因为准确,所以并没有多少饰词和喻词存在的必要,它们始于对具体事物进行的精细研究,又经过作者的反复锤炼。我们仿佛被作者拉着坐在那些无名老工匠的身边,目睹他们怎样把大地上的细碎材料耐心打造成人世的作品” 。我还没有听过其他人这样说,想必以为这不过就是图片说明一类。其实它是我写作中最费心力的部分,这里浓缩了我对研究对象的理解——是放到它生存环境中的理解,因此不论造型还是纹样,用词用字都力求与它的时代相合。在评述《棔柿楼集》的《文学与名物》里,张定浩注意到,“一件物品,每每出自平常日用,再因了个人的生命浸润而获得超越日常的诗意和礼仪,最后进入习俗,流转成为某种符号学意义上的程式图谱,这三层变化,并非单向度的,而是构成完整的循环,令扬之水念兹在兹,可以说是她名物学的核心” 。这的确是一种真正的理解。我想,所有的作者都不是希望听到多多益善的夸赞,而是希望理解与理解之后的批评,即知道我做了什么,进而指明欠缺。(本文图片为《定名与相知》书中插图)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